新规速递 |《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正式发布
新规速递 |《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正式发布
2019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2019年11月1日,为落实、保障《外商投资法》有效实施,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研究起草《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2019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实施条例》")正式发布。《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后,原有的三资企业法同时废止,《外商投资法》成为我国外资监管的基本法律,为我国的外资监管体系变革历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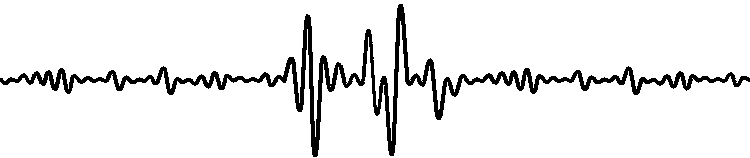
一、 重点内容简析
1.强调平等待遇及投资保护
《外商投资法》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在此基础上,《实施条例》进一步强调内外资平等待遇,例如:政府部门在政府资金安排、项目申报、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资质许可、标准制定等方面应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不得限制外资企业进入政府采购市场或实行差别及歧视待遇,不得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适用高于强制性标准的技术要求等。
沿袭《外商投资法》关于建立与完善外商投资保护制度之思路,《实施条例》具体落实强化投资保护的若干措施,包括明确征收条件与补偿标准、强调外汇自由汇入汇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此外,《实施条例》要求各地政府应当履行向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该等承诺应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此规定对实践中不时发生的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之目的开具"空头支票",或事后以有关承诺或政策违反法律法规、领导班子换届等原因拒绝履行承诺的情形进行了规范。
为确保贯彻落实上述要求,《实施条例》专设法律责任一章,明确在违反内外资平等待遇、违法限制外国投资者汇入汇出资金、拒绝履行承诺或承诺内容不符合法律法规等情形下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追责机制。通过该等制度之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规定的内外资平等待遇、投资保护等规定将得到更好的执行。
2.重塑外商投资监管体系
自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我国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与演变。在传统的审批制监管体系下,商务部门对于外商投资享有个案审批权,而发改委、工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外汇部门各自享有不同的备案、登记、核准或审批权限。该等审批安排不仅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造成沉重的负担,甚至在实践中对各方的有关商业安排产生干涉(例如,商务部门在审核交易文件时,有时要求各方修改投资协议、合资合同中包含的商业条款),各主管部门也有时因不同理解导致审批操作产生冲突(例如,工商部门有时会对已经商务部门批准生效的章程提出修改意见)。2016年,通过上海自贸区对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即负面清单)制度之试水,将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由个案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的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形成负面清单及关联并购之外的外商投资实行备案制的监管体系。该等监管体系虽已实现大幅简化,但仍然涉及工商和商务部门的两套登记/备案系统,各部门职能交错的状况未得以彻底改变。
《实施条例》在《外商投资法》的基础上重新梳理各主管部门的职能权限:除行业主管部门的行业许可外,发改委负责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而商务部门将不再拥有就外商投资及有关投资文件进行审核或备案的单独权限。值得注意的是,《实施条例》并未采取《征求意见稿》中拟定的将负面清单审核权限交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的监管思路,而是明确"有关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均可对拟议投资是否符合负面清单进行把关。仅从该条规定来看,这可能意味着多个部门审核职能的重合;但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来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已对其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查分工进行了预先协调[1]。我们期待未来各主管部门(特别包括发改委、商务部门)对该等审核分工问题进一步作出协调、澄清,以确保简化审查程序、统一审查标准。
3.中国籍自然人之股东身份
我国对中国籍自然人与外国投资者进行合资、合作的监管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逐步放开的过程。基于特定历史背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最初并不允许境内自然人与外国投资者进行合资、合作;后续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令")允许股权并购中境内公司的中国自然人股东经批准继续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局部突破前述限制。《外商投资法》第二条未对境内自然人作为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资格予以排除,为境内自然人成为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开了一道口子;而《实施条例》则直接明确,外商投资法所称"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国的自然人。至此,对中国籍自然人投资者的身份管控彻底放开。2020年1月1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颁发首张以中国籍自然人作为设立股东的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
4.信息报告制度
《外商投资法》生效前,即使是备案制外商投资企业,仍需通过两个路径报送信息,即商务部的外商投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企业登记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生效后,上述报送路径合二为一,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仅需通过企业登记系统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商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较大便利。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信息报告办法》")对信息报告制度进行细则性规定,其中明确,外国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将通过企业登记系统在线提交初始报告、变更报告,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在线提交年度报告;注销报告相关信息由市场监管总局向商务部共享,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无需另行报送。
5.过渡期
对于《外商投资法》赋予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的5年过渡期,《实施条例》删除《征求意见稿》中"6个月内变更"的宽限期,并明确在过渡期内未完成过渡变更的法律后果——现有外商投资企业逾期仍未依法调整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并办理变更登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其他登记事项,并将相关情形予以公示。
对于部分外国投资者担心的本次外商投资监管体系重大变更将可能导致动摇各方此前达成的商业基础的问题,《实施条例》亦提供一定解决方案: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依法调整后,原合营、合作各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股权或者权益转让办法、收益分配办法、剩余财产分配办法等,可以继续按照约定办理。该等规定使得合资、合作各方最为关心的利润分配及退出等事项能够继续沿用此前合同安排,可谓为中外各方开出一剂定心丸。
值得一提的是,若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未在5年内完成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的调整,其在5年期限届满后是否可继续适用原有组织架构?原有合资合同及章程是否继续有效?其按照原有组织架构所作出之决议是否具有法定效力?《实施条例》对该等问题并未予以明确解答,我们期待有关主管部门及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等问题予以后续澄清。
6.境内再投资
《外商投资法》将外国投资者的"间接投资"明确纳入监管范围。《实施条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适用《外商投资法》和《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
二、 留白问题探讨
除上述要点之外,我们亦注意到,《实施条例》对于部分问题采取简化或搁置处理。我们在此选择几点重要内容予以简要讨论,以飨读者。
1.VIE架构
除个别法规之外,我国法律对于协议控制架构("VIE架构")的监管一直处于灰色状态。2015年的《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曾尝试将"通过合同、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内企业或者持有境内企业权益"纳入外国投资之监管范畴,但可能考虑到该等举措将给实践中已广泛采用VIE架构的众多企业造成重大影响,最终《外商投资法》中并未沿用这一思路,而是在界定外商投资时采用较为模糊的"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表述,并增加兜底条款("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该等表述在《外商投资法》颁布之时亦曾引起一定讨论——若从严解读,则前述表述似乎亦可囊括VIE架构。相应地,《实施条例》是否会对该问题予以澄清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
《征求意见稿》虽未明确界定VIE架构是否落入其监管范畴,但尝试再次引入《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实际控制情形下视为内资"原则,即:中国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全资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的,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可以不受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的有关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限制。但是,正式公布之《实施条例》不仅删除了该条款,亦未对VIE架构的规范方式进行明确提及,VIE架构再次被搁置。我们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目前市场上广泛采取的VIE操作实践将按照现有方式继续保留。
结合上述立法进程及市场反响,我们能够看出,立法者虽数次尝试对VIE架构问题予以正面处理,但囿于VIE架构之普遍性、重要性以及境内外市场及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立法者仍然采取谨慎态度,并在新规中留有一定灵活性。未来待时机成熟之时,或许该问题会得以进一步澄清。
2.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之境内投资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实施条例》删除"华侨在中国境内投资,参照外商投资法和本条例执行"的表述,改为"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投资,参照外商投资法和本条例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考虑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曾专门发文从定居的角度对"华侨"之范围进行定义[2],本次调整是否意味着主管部门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审查主体范围?鉴于该规定将对持有境外身份的中国籍自然人之境内投资产生较大影响,我们期待实践中主管部门对"定居"之判断标准予以澄清,如是否沿用《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中对于"定居"的定义,或以境外永久居留权/拥有境外合法身份证件、拥有境外工作及/或习惯性居所、境外居住满一定年限等为判断标准。
3.关联并购
10号令第11条规定,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的公司,应报商务部审批,该条款建立了关联并购商务部审批制度。即使随着外资监管体系的不断改革,不涉及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资并购已不再受制于商务部门的事先审批,但关联并购(无论其投资领域)仍须经商务部审批。
如上文所述,《外商投资法》规定,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该规定并未明确排除关联并购,而《实施条例》亦未对关联并购进行特殊约定。但是,10号令本身并未被废止,《信息报告办法》亦要求在并购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形下,须明确报告该交易是否属于关联并购,这似乎又为关联并购继续受制于特殊监管要求留下一定空间。我们期待商务部对《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生效后10号令的效力以及关联并购的监管要求作出进一步的澄清。
4.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在《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生效前,我国尚无统一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而是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商务部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从并购角度对外资并购予以安全审查,并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的通知》,在部分自贸区范围内试行对涉及敏感投资主体、敏感并购对象、敏感行业、敏感技术、敏感地域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
《外商投资法》规定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但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实施条例》对此亦未进行任何细化。《外商投资》及《实施条例》生效后,有关主管部门会否基于前述规定出台审查细则,值得期待。
5.投资总额
传统上,外商投资企业具有独特的"投资总额"概念,其可在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即俗称的"投注差")范围内借用外债。《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均未明确提及"投资总额"之概念是否将得以保留,但国务院办公厅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有关投资总额之规定亦未被明确废止,且《信息报告办法》附件所列之报告信息仍然包括投资总额,我们理解《实施条例》发布后,外商投资企业应可继续按照现有方式选择通过宏观审慎模式或者在投注差额度内借用外债。
[注]
[1]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19年12年31日颁布、自2020年1月1日起生效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注册工作的通知》第一条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在登记注册前已经依法核准相关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的,登记机关无需就是否符合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规定条件进行重复审查。
[2] 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于2009年4月24日发布的《关于界定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规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且:(一)"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留权,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二)中国公民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5年内在住在国累计居留不少于30个月,视为华侨;(三)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包括公派和自费)在外学习期间,或因公务出国(包括外派劳务人员)在外工作期间,均不视为华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