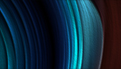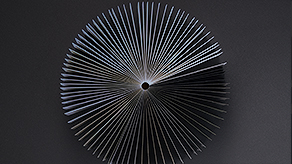争议案件中实质董事高管的身份认定
争议案件中实质董事高管的身份认定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修订的重要成果之一是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有益探索,并吸收域外法的成熟经验,进一步完善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合称“董监高")负有的忠实勤勉义务,其中也对实务界提出并关注的诸多问题均作出了切实回应,进一步夯实了以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为核心的董监高义务和责任体系。
本系列文章将结合本次修法的新增条文及过往司法实践,围绕哪些主体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忠实勤勉义务在实践中的基本要求、违反忠实勤勉义务如何追责等争议话题展开分析,以期从争议解决的角度为董监高履职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操建议。本文为本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我们将主要聚焦于董事及高管的身份认定问题。
一、事实董事制度的新设和重述
(一)现行《公司法》与新《公司法》关于董事主体认定标准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以下简称“现行《公司法》")对于董事的认定,基本采取了形式主义模式中的任命标准:在程序上,第37条规定股东会有权选举、更换非职工代表董事,第44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在实体上,第146条规定了董事的任职资格,违反该规定的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与此同时,司法实践多数认为董事的认定以公司内部决议为准,是否对外完成工商登记并不影响董事身份的认定[1]。
我们认为,这一形式标准虽然便于识别董事身份,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未经选任、选任过期或者选任存在瑕疵,但实际履行董事职责的人员(以下合称“非形式董事"),是否负有忠实勤勉义务并承担违反忠实勤勉义务后的责任?尤其在我国公司治理普遍不完善、工商登记与内部情况有时存在错位的情况下,这一重角色责任、轻行为责任的追究机制,将直接导致非形式董事因其身份角色而逃脱其本应承担的行为责任[2],这显然不利于公司治理和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为解决形式主义模式下的通行问题,实质主义的立法模式应运而生。后者认为,无论是否经正式登记或任命、只要在事实上持续履行董事职责即应认定为董事。[3]事实上,在新《公司法》修订前,我国司法实践已经开始积极探索,部分案例在说理中尝试引入事实董事的概念来重新划定董事义务及承担相应责任[4]。其中,较为明确的阐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裁判指引》(桂高法民二〔2020〕19号)第34条的规定:“任何实际上享有或行使董事高管职权的人员,都可以属于勤勉义务的责任主体。具体有两类情形:……(2)不显名的实质适格。例如股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在公司中显名任职,但在公司经营中却实际享有管控与决策权,他们实质上行使了公司董事高管的职权,因为股权本身并无直接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能,故不应简单依据《公司法》第20条来判断其是否滥用股东权利而承担相关责任,而是应当以公司法及章程关于董事高管的忠实与勤勉义务作为判断标准。"
在此基础上,新《公司法》吸收了前述有益的司法实践,并在立法层面首次引入了域外法上的两类实质董事: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
(二)关于事实董事的认定要件
事实董事是指实际执行董事职务之人[5]。新《公司法》第180条第3款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前两款规定(即董事义务)"。
1. 主体要件:限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新《公司法》第180条第3款将主体限定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这一立法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我国公司治理的普遍现状:多数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高度重合,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操纵董事和高管、不当介入公司经营管理,并进而产生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公司治理困境。
但值得关注的是,域外法对于事实董事的认定通常着眼于非形式董事是否从事了董事行为,一般并不审查或者限制其主体身份[6],但新《公司法》将事实董事的主体限定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强调行为人对公司的支配行为(包括投资关系、协议关系和其他安排)[7],而“实质董事"则强调行为人行使董事职权或指使董事行为,二者对于介入公司治理方式的关注点不同,在实践中也并不当然重合。试举一例,作为小股东的国资股东或财务投资人向目标公司委派的董事,其履行董事职责很可能受到股东方的操控,但此时前述小股东在新《公司法》项下并不会承担董事责任。再如,实践中家族企业数量众多,很多时候实控人的配偶、子女或其他重要亲属虽不在企业担任董事,但事实上行使董事职权,新《公司法》亦未提供向该等主体追究董事责任的路径。由此可见,这种限定事实上遗漏了非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行为人从事董事行为的情形,会部分减损事实董事制度的实际效用。
2. 行为要件:实际执行公司事务
行为人在何种情形下构成事实董事,也即如何理解本条规定的“实际执行公司事务",应当是指行为人实施公司董事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具体包括新《公司法》第67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职权内的各项事宜。实务中的情形通常包括以董事身份参与董事会会议表决、以董事身份在公司文件上签字、作为执行董事行使董事会职权等。[8]这也与域外法的经验基本一致[9]。
二、影子董事/高管的认定要件与责任分担
(一)关于影子董事/高管的认定要件
新《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知,影子董事/高管是指公司董事/高管在执行公司事务时遵循其安排、听从其指令之人[10],这一概念亦为新《公司法》首次在立法层面正式引入。
1. 主体要件:限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同前述新《公司法》中的事实董事规则所述,第192条也将主体限定在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如前所述,这种限定身份的立法模式虽响应了实践需求,但也遗漏了非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行为人指示董事/高管行为的情形,同样减损了影子董事/高管制度的实际效用。
2. 行为要件:“指示"+“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
(1)关于“指示"的认定要点
从内容上来看,是指对他人进行开导、说服或通过刺激、利诱、怂恿等行为,最终促使公司董事/高管接受行为人的意图,进而实施某种加害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新《公司法》第192条的规定相对明晰简洁,删去了一审稿中“利用其对公司的影响"的表述,仅保留“指示"这一行为要件。故从文义出发,对于此处“指示"的理解,是否需要考察影子董事/高管的控制力强度、指示或命令的范围、被指示董事习惯性遵循的频次[11]、指示的频次和持续性等因素,法律并未明确,未来将有赖于通过司法实践形成可资参考的经验。
从方式上来看,指示可以分为明示和默示,明示包括书面的决议或批示、聊天记录等[12];默示又分为推定和沉默,前者是指从行为人作出的特定积极行为推定其意思表示,应该属于此处“指示"。但对于行为人的单纯沉默(消极不作为)是否可以属于“指示",还需要探讨该条对于影子董事/高管的规制基础是基于公司法项下的忠实勤勉义务,还是侵权规则在公司法中的具体及特别规定。就后者而言,行为人负有的是“教唆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侵权责任,但因消极的不作为不能成立教唆行为,故此时沉默不能被认定为本条的“指示"行为。
(2)关于“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认定要点
此处“损害公司利益"的认定,主要对应新《公司法》第181条至第184条概括并列举的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情形。
此处“损害股东利益"的认定,应当与新《公司法》第190条所涉情形一致,均指向狭义的股东利益损害,即不影响公司整体利益的股东利益损害,并不包括因公司利益受损导致的股东利益间接损害。例如损害股东的身份权、知情权、表决权、分红权等专属于股东的权利。实务中常见的具体情形包括“不当地稀释股东的股权",“在股东会会议的筹办过程中未及时通知股东,使股东未能行使表决权,从而使公司形成了有损于其利益的决议"[13]等。
(二)路径争议:忠实勤勉义务的违反还是教唆侵权责任的特别规定?
尽管修法后多数观点(如参与修法的赵旭东教授与刘斌教授)将新《公司法》第192条界定为影子董事规则,但与域外法中传统的影子董事规则不同的是,该条仅从法律后果的角度规定了行为人对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与董事承担连带责任,并未同第180条所述,正面确认事实董事负有与形式董事相同的忠实勤勉义务。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新《公司法》第192条并非影子董事规则,而是侵权法规则在公司法中的具体化和特别规定,即行为人负有的是“教唆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侵权责任。
基于这一法律解释分歧,未来在法律适用中,行为人在承担的责任类型和方式上还可能产生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争议:第一,行为人是否承担新《公司法》第186条规定的收入归入责任?第二,行为人是否须根据新《公司法》第191条之规定,对公司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行为人是否需承担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这一系列的争议,都将有待于未来实践的检验,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并和读者分享。
(三)责任分担:影子董事/高管与形式董事/高管的内部责任份额
新《公司法》明确,影子董事/高管应“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但关于该连带责任内部份额如何确定,有观点基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决策的实质性影响,认为应当确立二者间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即在对外承担责任后,由影子董事/高管最终在内部关系中承担全部份额。
但相比于这种一刀切的责任推定分配,参与本次修法学者的观点更符合多数人侵权的基本分析框架,也可能代表未来更主流的裁判趋势:“在责任分配方面应当重点考量控股股东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损害造成的作用力和自身过错两方面内容,在个案中具体分析二者对损害行为产生的作用以及自身在主观上的过错程度来确认责任分配比例"[14]。依据这一观点,影子董事/高管与形式董事/高管之间很可能会承担按份连带责任,这样的观点亦有利于董事真正地为公司的利益来行使职权,从而促使我国公司治理实践的进步。
三、关于事实高管认定的司法探索
(一)新《公司法》对于事实高管规则的回避
较为遗憾的是,相较于新《公司法》第192条明确引入了“影子高管"的概念,第180条第3款仅规定了事实董事,而回避了事实高管的情形。这一区别这属于法律漏洞,亦或是有意排除,有待进一步明确。但一方面,在过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管的认定在现行《公司法》规定基础上的确存在法院自由裁量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鉴于明确法律依据的缺乏,法院如果拟要求实质承担高管职责、但又非形式意义上的高管承担责任,可能仍将参照现有做法,更多依赖于对“高管"概念的个案解释。
(二)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高管认定的探索与分歧
在既往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通常首要的争议问题是案涉员工是否构成公司法定义下的“高管",但因实践中多数公司的章程并不会对高管进行明确列举,故如何对新《公司法》第265条〔即现行《公司法》第216条,下同〕规定以外的管理层人员主张违反忠实勤勉义务后的赔偿责任,往往存在极大争议。
结合我们在各地法院的办案经验,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管身份的认定存在两类观点,一类观点认为应当严格依据新《公司法》第265条的规定进行认定,不进行实质判断或类推解释;另一类观点则主张采实质判断标准进行认定,并发展、细化出多种审查要素。
1. 坚持文义解释,严格依据新《公司法》第265条认定高管身份
新《公司法》第265条第1款明确将高管定义为“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部分司法判例据此认为,高级管理人员是一个法定概念,应当采文义解释路径、严格依据该条进行认定,避免将本来并非高管的劳动者认定为高管,不当加重劳动者的负担,造成劳资关系的失衡。即便部分工作人员身处管理岗位并享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也并不当然地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管范畴。[15]
2. 对新《公司法》第265条的进行类推解释,形成高管身份的认定标准
尽管新《公司法》第180条第2款暂未明确“事实高管"的规制情形,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亦有较多的法院倾向对新《公司法》第265条进行类推适用,将实际执行高管职务的人员扩张解释为高管,并课以忠实勤勉义务。根据对既往案例的梳理,司法实践认定构成事实高管的标准主要包括:
(1)对公司整体业务具有经营决策权的人员[16];
(2)对公司重要事务(人事任免/考核、财务报销/预算/决算、代表公司对外谈判或签署合同)具有决策权的人员,或者担任重要部门的负责人[17]。
在此基础上,通过哪些证据或事实可以用以证明前述标准,我们亦对司法实践中较常见的审查要素做了如下梳理,包括但不限于:
劳动合同、任命文件、聘书等载明的职务职级信息和工作内容;
内部汇报层级、任职部门在公司组织架构所处位置;
员工通讯录分组信息;
名片、邮件签名等对外文件中的职务职级信息;
薪资待遇是否符合同行业同类高管的水平等。
鉴此,从争议解决角度来看,在此类高管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代理公司的一方可以强调实质判断标准,从案涉管理层人员对公司整体业务或重要事务享有经营决策权等角度着手,论证其属于高管进而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代理员工的一方则可以强调认定高管身份应当严格坚持文义解释,随意类推解释将课以劳动者不合理的义务。从公司内部治理及合规要求的角度来看,建议公司将实质享有一定经营决策权的管理层人员载入章程中,并规范相关的任免程序及内部架构,从而避免管理层人员权责不明以及因此产生的潜在风险。
小结
本文主要介绍了法律及司法实践中对于忠实勤勉义务的责任主体,特别是本次修法中新增的事实董事/高管、影子董事/高管的法定范围及认定标准。待新《公司法》施行之后,这一新增制度的适用在未来司法实践中会衍生出哪些争议,又会形成怎样的司法裁判标准,尚待实践来检验,本文仅试图在基于既有办案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试论。但公司治理实践纷繁复杂,衍生的争议案件亦各不相同,我们将保持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并及时更新梳理、以飨读者。
[注]
[1] 参见(2014)民申字第2136号、(2019)粤民申6579号、(2017)京民终472号、(2009)沪一中民三(商)终字第548号等案例。
[2] 赵旭东:《中国公司治理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现代法学》2021年第2期。
[3] 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页。
[4] 参见(2017)最高法民终869号、(2021)京0116民初7599号等案例。
[5] 在类似的立法例中,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250条规定,所谓董事包括任何占据董事职位之人,而不论其称谓为何。《澳大利亚公司法》第9条规定,公司董事是指依法选任的董事、事实上执行董事职务者,以及董事习惯于听从其指令或意愿者。《新加坡公司法》第4条规定,董事包括以任何名义担任公司董事的任何人,以及公司董事或大多数董事习惯于听从其指示或指令的人,以及候补或替代董事。
[6] 刘斌:《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
[7] 这种支配行为具体分为:一是投资关系,如“通过投资目标公司的母公司等,实现对该公司的支配";二是协议关系,如“与公司签订协议彻底控制其原材料来源、销售渠道等,迫使目标公司借此维持存续,进而支配目标公司",“签订对赌协议后入驻目标公司进行控制"以及“通过与股东或者董事、经理的协议控制公司经营"等;三是其他安排,如“通过对董事、经理的任免,与公司股东、管理层的亲属关系,作为公司实际经营者等支配公司"。
[8] 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第1版,第389~390页。
[9] 例如,英国法的判断标准是,行为人是否构成“公司治理框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否具备董事的地位和职责"。
[10] 在类似的立法例中,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251条规定,影子董事是指公司董事遵循其指示(directions)或指令(instructions)而行事之人。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第9条规定,公司的董事包括,(除非表达了相反的意思),一个没有正式被委任为公司董事的人,但公司的董事习惯于遵循其指令(instructions)或意愿(wishes)而行事。新加坡1993年《公司法》第4条规定,董事包括以任何名义担任公司董事的任何人,以及公司董事或大多数董事习惯于听从其指示或指令的人,以及候补或替代董事。我国香港地区《公司条例》第2条规定,就法人团体而言,影子董事指该法人团体的一众董事或过半数董事惯于按照其指示或指令(不包括以专业身份提供的意见)行事的人。
[11] 丁亚琪:《实质董事的规范结构:功能与定位》,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4期。
[12] 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第1版,第424页。
[13] 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第1版,第425页。
[14] 赵旭东主编:《新公司法条文释解》,法律出版社2024年第1版,第425~426页。
[15] 参见(2021)最高法民申3624号、(2022)京01民终6951号、(2018)粤01民终10460号等案例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经验及类案裁判方法通报之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的审理思路和裁判要点》(2020年第43期)。
[16] 参见(2021)最高法民申6043号、(2019)最高法民申2728号、(2021)京01民终7044号、(2020)京03民终8429号、(2017)沪01民终12579号等案例。
[17] 参见(2018)粤民申10433号、(2022)京03民终5329号、(2020)粤01民终4015号、(2020)苏12民终2050号、(2023)京03民终3803号、(2020)粤01民终21724号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