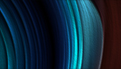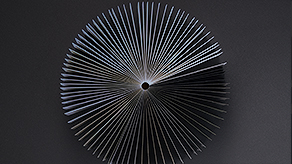不止于反洗钱:《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管理办法》的制裁属性与合规影响
不止于反洗钱:《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管理办法》的制裁属性与合规影响
2026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26年2月16日起施行[1]。
《管理办法》通过官方名单触发、自动冻结、控制关系穿透及持续适用等制度设计,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系统性确立了一套具有金融制裁等效效果的国内执行机制。该办法不仅显著扩展了传统反洗钱措施的适用边界,而且在功能上承担起我国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定向金融制裁义务、实施自主金融风险隔离措施的重要制度角色。
与此同时,伴随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及其配套制度(包括资产冻结/限制交易措施、不可靠实体清单及反制清单)的逐步完善,《管理办法》在国内制裁体系中与外部制裁应对形成互补,为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跨境经营企业提供了系统化合规路径。本文从制度定位、核心规则、执行机制及合规影响等角度,系统分析其对金融机构与非金融市场主体的深远影响,以期为相关市场主体提供实务指引。
一、立法背景与制度定位
从立法背景看,《管理办法》的出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我国在国际反洗钱、反恐融资与防扩散融资义务持续强化背景下,对既有制度体系进行系统整合与功能升级的重要举措。首先,在反洗钱反恐融方面,2019年FATF第四轮互评估显示中国在定向金融制裁执行方面存在改进空间。特别预防措施制度的建立是中国迎接新一轮FATF评估、提升合规水平的关键举措,旨在实现从“部分合规”向“完全合规”的转变。其次,国际社会对金融制裁执行的合规要求不断提高,联合国安理会定向金融制裁措施在成员国国内法层面的可执行性受到高度关注。
此前,除反恐融等特别名单的绝对禁止以外,其他名单维度的风险控制均需要和反洗钱控制措施进行衔接,由于审核流较长会导致风险外溢。在此背景下,《管理办法》并非简单扩展反洗钱监管范围,而是引入了一套以名单为中心、以资产冻结和服务禁止为核心手段的风险隔离机制。其制度逻辑已明显不同于一般反洗钱规则,更接近国际金融制裁的执行模式。
在制度沿革层面,《管理办法》对2014年施行的《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进行了实质性升级:一方面,适用对象不再局限于恐怖活动相关主体,而是扩展至恐怖融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融资以及具有重大洗钱风险的其他对象;另一方面,其直接承接外交部发布的联合国安理会定向金融制裁名单,使国际制裁在我国境内获得明确、可直接适用的国内法执行基础。
因此,《管理办法》除了属于反洗钱新规以外,也是我国在国内法层面系统构建金融制裁执行机制的重要制度节点,并与《反外国制裁法》及其配套制度形成制度互补,为跨境金融及交易活动提供法律和操作支撑。
二、《管理办法》的制度结构与运行机制
(一)制度结构
《管理办法》共五章三十一条,分别为总则、名单与执行、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其条款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制裁执行规则特征。
首先,在触发机制上,《管理办法》以官方名单作为采取措施的唯一法律依据。义务主体无需、亦不得自行评估名单对象是否存在具体违法行为,而应在发现匹配时立即执行措施。
其次,在措施性质上,《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冻结和服务禁止并非临时性或审慎性处置,而是具有强制性、即时性和持续性的法律义务。
再次,在制度目标上,《管理办法》并不以调查或惩罚为目的,而是通过切断资金、资产及服务供给,对高风险对象实施前置性、预防性的风险隔离。这一目标与金融制裁制度高度一致。
(二)适用主体
《管理办法》在适用主体设计上,体现出明显的扩张性与普遍性。
金融机构仍是最核心的义务主体。第三章“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规定,金融机构须建立健全与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相匹配的内部控制制度,持续开展名单筛查,并在发现匹配时立即冻结相关资产、停止提供服务并依法报告。
与此同时,《管理办法》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在从事特定业务时,应参照金融机构履行同等义务[2]。该等主体包括房地产中介、贵金属和宝石交易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公证机构等[3]。对上述主体而言,《管理办法》意味着其在特定业务场景下被直接纳入类制裁执行链条。
更为关键的是,《管理办法》通过第二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将义务扩展至“任何单位和个人”,涵盖中国公民、依法设立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及其境内外分支机构。这一安排使制裁执行不再局限于金融监管领域,而是上升为普遍适用的国内法义务,显著拓宽了合规责任的外延。
与之配套,《反外国制裁法》及不可靠实体清单、反制清单制度则对境外交易主体、境外供应链及外部制裁风险进行管理,实现国内制裁与外部制裁风险防控的协同。
(三)限制对象与名单体系
在限制对象层面,将限制目标限定于法定的三类官方名单。根据《管理办法》第二条,限制对象包括:
其一,国内反恐名单。由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并公告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延续既有反恐资产冻结制度。
其二,联合国安理会定向金融制裁名单。该类名单在国际法上本质即为金融制裁措施,《管理办法》通过直接承接外交部发布的相关名单,使其在我国境内具备明确、统一的执行基础。
其三,中国人民银行自主或会同认定的重大洗钱风险名单。该类名单体现了我国在履行国际义务之外,基于国家金融安全需要实施自主风险隔离措施的制度空间。
需要关注的是,由于《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与解释,因此,除关注人行银行发布名单外,也需要同步关注其他机构已发布及拟发布名单。通过上述设计,《管理办法》在国内法层面整合了国际制裁、反恐融资与自主金融限制三类风险来源,形成了统一的名单执行框架。
(四)穿透适用与反规避规则
《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不仅适用于名单对象本身,还延伸至其代理人、受其指使的主体,以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组织。
该穿透适用规则相比于传统反洗钱中常见的“关联交易审查”,更接近制裁反规避机制。其制度逻辑与国际制裁实践中的“所有权或控制测试”高度一致,旨在防止通过复杂股权结构、壳公司安排或中间人机制规避冻结措施。
对义务主体而言,这意味着合规审查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形式上的交易对手,而需实质性识别控制关系与实际受益人。
同样,《反外国制裁法》及《不可靠实体清单》等规定也强调对境外关联方、供应链中间人及控制主体的识别,二者在实际操作中可形成协同审查机制,强化对规避行为的防控。
(五)特别预防措施的内容及其制裁属性
《管理办法》规定的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集中体现为两项核心义务:
(1)立即停止提供金融等服务或者资金、资产;
(2)立即限制相关资金、资产转移。
需要注意的是,《管理办法》对“资金、资产”的界定极为宽泛,涵盖有形和无形资产、动产和不动产、传统金融资产与数字化权益,并明确包括资产孳息和未来收益。[4]
从法律效果看,该等措施与国际金融制裁中的全面资产冻结和服务禁令具有实质等同性。一经触发,义务主体不享有是否执行的裁量权,其合规义务具有高度刚性。
(六)时间规则与持续义务
《管理办法》要求义务主体在名单发布或调整、客户准入、一次性服务、客户信息变更等多个节点持续开展筛查。根据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义务主体须在以下情形主动开展核查并执行措施:
(1)官方名单发布或调整时;
(2)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时;
(3)提供一次性金融服务时;
(4)客户身份基本信息发生变更时。
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一经采取,即持续有效,直至满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三项法定解除条件之一(名单移除、核实有误、法定程序认定解除),才能使该等措施转变为常态化合规义务。
(七)管辖范围
《管理办法》的管辖范围兼具属地与属人原则。就属地原则而言,《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其明确适用于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就属人原则而言,其明确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及其境内外分支机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境外经营中,亦需同步评估《管理办法》项下的交叉合规风险。在合规效果层面,该种安排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类似单边制裁规则的外溢影响。
(八)解除、豁免与法律责任
《管理办法》规定措施并非永久性,其解除严格基于以下法定情形:
(1)规定的名单发生调整,相关组织或者人员不再属于名单范围;
(2)经核实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有误;
(3)经相关部门通过法定程序认定需要解除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
同时,《管理办法》设置了基本生活支出及合同履行相关的有限豁免机制,允许在严格审批、用途限定和持续冻结前提下,使用部分被限制资产。需要强调的是,该类豁免并非对制裁强度的放松,而是高度程序化、个案化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避免措施产生不必要的次生社会影响,而不改变资产整体冻结的法律状态。
此外,《管理办法》通过直接衔接《反洗钱法》的处罚体系,确立了严格的机构责任与个人责任并行的问责机制。对于金融机构,若违反本办法规定,将直接依据《反洗钱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进行处罚,包括罚款,并可在第五十六条授权下“双罚”至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对于特定非金融机构,由其主管部门依《反洗钱法》第五十八条处罚。对于监管人员,第二十五条规定泄露保密信息将依法给予处分。
三、合规应对与实务建议
《管理办法》的实施,意味着市场主体在合规实践中不仅需满足传统反洗钱意义上的“风险为本”要求,而是需要正面应对具有金融制裁等效效果的强制性风险隔离要求。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及为其提供专业服务的中介结构,均有必要对现有合规体系进行针对性调整。
(一)金融机构:从反洗钱流程管理向制裁执行能力建设转型
对金融机构而言,《管理办法》的核心挑战不在于新增合规义务的数量,而在于义务性质的转变。
首先,应系统整合反洗钱与制裁名单管理机制。金融机构需建立覆盖国内反恐名单、联合国安理会定向金融制裁名单、中国人民银行自主与会同认定名单的统一筛查体系以及反外国制裁法相关清单,并确保该体系与客户准入、持续尽职调查及交易监测流程深度嵌合,避免因名单来源分散或更新不及时导致执行漏洞。
其次,应完善“自动触发、立即执行”的内部操作规则。《管理办法》明确排除了“未收到监管指令”作为免责事由,要求金融机构在发现匹配情形时即刻采取冻结和服务禁止措施。因此,内部制度应清晰界定触发标准、操作路径及权限分工,确保一线业务部门在技术匹配触发后具备即时处置能力。
再次,应高度重视控制关系和穿透审查能力建设。鉴于《管理办法》明确适用于名单对象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组织,金融机构在尽职调查中需强化对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及关联结构的识别,防止因形式合规而实质违反制裁执行义务。
最后,应通过完善留痕与内部问责机制,降低事后合规风险。在名单匹配存在边界不清或误伤可能的情形下,详实、可追溯的内部记录是证明审慎履职、应对监管检查的重要依据。
(二)特定非金融机构与一般企业:将制裁筛查纳入关键业务节点
对特定非金融机构以及与高风险对象存在交易可能的一般企业而言,《管理办法》释放出的信号在于:制裁合规不再是金融机构的专属义务。
一方面,特定非金融机构在从事法律服务、会计服务、房地产交易、贵金属交易等业务时,应在客户准入和交易执行前引入必要的名单筛查与背景核查机制。即便未建立与金融机构同等复杂的系统,也应确保在关键节点具备合理、可证明的筛查流程。
另一方面,一般企业在跨境交易、投融资、并购重组、长期供货或代理安排中,也有必要评估交易对手是否涉及《管理办法》项下的名单对象或其控制实体。尤其在涉及资金、资产或持续性服务安排时,应通过合同条款、尽职调查及持续监控等方式,预先识别并隔离潜在制裁风险。
此外,企业还需注意《管理办法》关于“不得事先通知”的规定,避免在交易磋商或内部沟通过程中,因不当信息披露而引发合规风险。
总体而言,非金融主体虽不承担与金融机构同等强度的合规义务,但在关键业务节点建立基本的制裁筛查与风险隔离机制,已成为合规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
四、总结
《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反洗钱制度在功能定位上的重要提升。该办法通过以官方名单为核心、以资产冻结和服务禁止为主要手段的制度设计,在国内法层面确立了一套具有金融制裁等效效果的风险隔离机制。同时,伴随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及其配套制度的逐步完善,《管理办法》在国内制裁体系中与外部制裁应对形成互补,为跨境经营企业提供了系统化合规路径。
从制度结构看,《管理办法》直接承接联合国安理会定向金融制裁名单,并通过自动触发、穿透适用和持续冻结等规则,构建了高度刚性的执行体系。相关措施并不以个案违法认定为前提,而是以名单状态为触发条件,这一运行逻辑决定了其在合规实践中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和即时性。
从适用范围看,《管理办法》突破金融监管的行业边界,将义务扩展至特定非金融机构乃至“任何单位和个人”,并通过属人管辖原则一定程度延伸至与中国存在连接点的机构。制裁合规因此被内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内法义务,对市场主体的合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实践影响看,《管理办法》推动合规管理重心由事后应对转向事前识别与持续监控。金融机构需强化制裁型风险隔离的执行能力,非金融主体和一般企业亦有必要在关键业务节点引入基本的名单筛查和风险评估机制。
总体而言,《管理办法》并非一部单纯的反洗钱新规,而是在反洗钱法律框架下运行的金融制裁执行规则。其实施不仅拓展了反洗钱制度的功能边界,也对市场主体的合规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注]
[1] 中国人民银行 外交部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2026〕第1号(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管理办法)。
[2] 第二十四条 特定非金融机构在从事规定的特定业务时,参照本办法关于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的相关规定,根据行业特点、经营规模、洗钱风险状况履行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义务。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六十四条 在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履行本法规定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
(一)提供房屋销售、房屋买卖经纪服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房地产中介机构;
(二)接受委托为客户办理买卖不动产,代管资金、证券或者其他资产,代管银行账户、证券账户,为成立、运营企业筹措资金以及代理买卖经营性实体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
(三)从事规定金额以上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
(四)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洗钱风险状况确定的其他需要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
[4] 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详细界定,被限制的“资金、资产”范围极其广泛,涵盖任何形式的有形或无形资产、动产或不动产,并通过列举方式明确包括银行存款、票据、邮政汇票、保单、提单、仓单、信用证,股票、债券及其他证券,房屋、土地、车辆、船舶、货物,石油等经济资源,其他以电子或者数字形式证明资产所有权、其他权益的法律文件、证书等,潜在可用于获取资金、商品或者服务的任何其他资产,以及资产产生的孳息和其他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