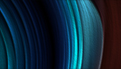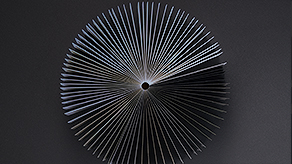以案说法 | “重大不利影响”条款之“重大”解析(下)
以案说法 | “重大不利影响”条款之“重大”解析(下)
引 言
作为交易律师,笔者始终认为,对交易文件模板和范本不经检讨的拷贝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密切关注法院对有关交易条款的解释和裁判尺度,正确理解有关交易条款背后的法理基础,恰当预判有关交易条款的法律后果,才能在代表客户起草、谈判和修改交易文件过程中,真正识别和防范法律风险,切实保护客户的利益。为此目的,笔者基于2018年10月1日特拉华州衡平法院(The Delaware Court of Chancery)对Akorn v. Fresenius一案作出的判决意见以及自身的经验与思考,通过本文对"重大不利影响"条款进行全面的梳理,以期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有些冗长,为便于阅读,遂分为上下两篇:上一篇笔者对 "重大不利影响"的定义、"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内容和"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作用进行阐述和分析;本篇将对"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法理基础、美国法院涉及"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判例和Akorn v. Fresenius一案的判决意见进行探讨和整理。管规之见,难免粗陋,切盼同仁指正。
四、"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法理基础
并购交易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并购协议。并购协议是并购方与标的公司或出售方之间为实现并购目的通过谈判达成的合同,对并购交易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的约定。并购协议受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的规范,与其他种类的合同相比,具有其特殊性。然而,并购协议作为合同的一种,与其他任何合同一样,需遵守合同法的一般原则。
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合同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如果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将承担违约责任。然而,作为"合同必须遵守"原则的例外,合同法允许在出现某些极端情形时,合同一方可以免于履行合同而无须承担违约责任,例如"履约不能"(Impossibility or Impracticability)和"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
(一)
履约不能
"履约不能"是指合同签订后,发生某些极端事件或出现重大情势变更,致使合同一方履行合同成为不可能(Impossible)或变得极端不合理地困难(Extremely and Unreasonably Difficult)。在此情形下,该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或免于履行合同义务,并无需因此承担违约责任。"履约不能"可以分为"客观上的履约不能"和"主观上的履约不能"。前者是指合同一方履行合同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不可能,后者指合同一方履行合同变得极端不合理地困难。
"履约不能"被认为构成不可抗力条款的合同法基础。[1]绝大多数的商事合同都包含不可抗力条款,而且,不可抗力条款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合同条款,通常约定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形下,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可以延迟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另外,"履约不能"也被视为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势变更原则"的法理基础。[2]
有权援用"履约不能"而主张免于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的一方是遭受"履约不能"情形影响的一方,也就是其履行合同义务成为不可能或变得极端不合理地困难的一方,该合同一方通常是履行体现合同特征之义务的一方,如买卖合同中的卖方、服务合同中的服务提供方、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等,而非支付价款、报酬或租金的一方。
(二)
目的落空
"目的落空"是指合同签订后,发生某些难以预料的异常事件或出现重大情势变更,使合同一方签订合同的主要目的不能实现或基本上不能实现。在此情形下,该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或免于履行合同,并无需因此承担违约责任。[3]与"履约不能"相反,依据"目的落空"免除合同一方履行合同的责任,不是因为该一方履行合同成为不可能或变得极端不合理地困难,而是因为对其来说合同对方的履行变得没有价值或者基本上没有价值。"目的落空"被认为是"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合同法基础。
有权援用"目的落空"而主张免于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的一方,通常不是履行体现合同特征之义务的一方,而是为该一方的履行付出对价的另一方,如买卖合同中的买方、服务合同中的服务接受方、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等。
不论是"履约不能"还是"目的落空",作为合同法之基石-----"合同必须遵守"原则之例外,是特定情形下的一种衡平救济措施,因而其适用必须满足非常严格的条件,并且限于非常极端的情形。否则,如果频繁适用该等例外情形,将严重侵蚀合同法的基础。
然而,虽说"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法理基础是"目的落空",但并购协议中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并非合同法"目的落空"原则的简单复制。正如Akorn v. Fresenius一案的判决书所称:如果认为并购交易中精明的各方当事人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律师费起草和磋商"重大不利影响"条款仅仅是为了在并购协议中重述合同法"目的落空"原则,这是非常不合情理的。[4]相较于合同法"目的落空"原则要求一方签订合同的"主要目的完全或者近乎完全落空"这一严苛的条件,并购协议中各方商定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可以约定较低的适用条件。因而,在判断"重大不利影响"是否发生时,应基于并购协议中关于"重大不利影响"的定义,而非合同法"目的落空"原则的固有含义。
五、涉及"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法院判例
"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是普通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就美国而言,一家美国法院做出的判例,对该法院自身及其下级法院审理同类案件具有约束力,对其他法院审理同类案件具有说服力。[5]"重大不利影响"作为商事交易当事方创设的条款,由于其本身含义的模糊性,其适用完全取决于法院的解释。因而,法院以往做出的涉及"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判例,对理解和判定"重大不利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如前所述,美国法院做出的涉及"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判例并不是很多。在Akorn v. Fresenius一案之前,作为公司纠纷诉讼重地的特拉华州法院,尚未有一项判例认定"重大不利影响"的发生。但是,特拉华州法院在Akorn v. Fresenius一案之前做出的涉及"重大不利影响"的不多的判例中,In Re IBP一案[6]和Hexion v. Huntsman一案[7]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判例。在Akorn v. Fresenius一案之前,该两个案件的判决意见一直是解释和判定"重大不利影响"的标杆。
(一)
In Re IBP案
In Re IBP一案是特拉华州衡平法院于2001年6月15日就Tyson Foods并购IBP的并购交易纠纷做出的判决。案涉标的公司IBP是美国排名第一的牛肉经销商和排名第二的猪肉经销商。通过竞购,美国排名第一的鸡肉经销商Tyson Foods击败美国排名第一的猪肉经销商Smithfield Foods,于2001年1月1日与IBP签订《合并协议》,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并购IBP,以期成为全球最大的肉食供应商。
2000年冬天和2001年春天,Tyson Foods自身的业绩表现惨淡,同时,IBP的经营状况也出现严重下滑。两家公司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严寒的天气导致的活禽供应短缺。随着困境不断恶化,Tyson Foods完成并购交易的愿望逐渐冷却。随后,Tyson Foods试图与IBP磋商降低并购价格,未果。2001年3月29日,Tyson Foods发函给IBP,宣告终止交易,并于当日向阿肯色州(Arkansas)法院起诉IBP。次日,IBP向特拉华州法院起诉Tyson Foods,要求履行《合并协议》。
在诉讼中,Tyson Foods声称IBP于2000年最后一个季度和2001年第一个季度糟糕的业绩(2001年第一个季度的每股盈利比2000年同期下降64%)证明IBP发生"重大不利影响",因而其有权根据《合并协议》中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解除《合并协议》。值得注意的是,In Re IBP一案的《合并协议》中关于"重大不利影响"的定义并未包含许多并购协议中所通常包含的除外情形,如整体经济、相关行业、恶劣天气、市场情况等引起的变化。
法院认为,对一个长期的战略投资者而言,标的公司的业务和经营业绩发生"重大不利影响",必须是对其在"商业上合理的期限"(A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Period)内的盈利能力具有重大实质影响,而该"商业上合理的期限"应当用"年"而非"月"来衡量。[8]如果一个战略投资者视短期的暂时性变化构成重大不利变化,这是非常不合常理的,除非该暂时性的变化或其成因对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法院进一步认为,"重大不利影响"条款是为了在发生严重危及标的公司较长期限内整体盈利能力的未知事件时,对并购方提供保护。标的公司盈利的短期暂时性不利变化不足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应从一个理性的并购方的长远角度来审视。[9]
然而,法院在做出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判定时,似乎有些纠结。在法院看来,如果IBP在2001年第一季度糟糕的业绩表现持续下去,很难说IBP未发生"重大不利影响"。但法院指出,Tyson Foods没有提供证据证明IBP的价值或盈利能力因2001年第一季度糟糕的业绩表现而被严重削弱。最后,法院认定,Tyson Foods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IBP发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
Hexion v. Huntsman案
Hexion v. Huntsman一案是特拉华州衡平法院于2008年9月29日就Hexion并购Huntsman的并购交易纠纷作出的判决。Hexion和Huntsman是两家全球性的化工产品制造商。在金融危机即将爆发之前的2007年7月12日,Hexion与Huntsman签订《合并协议》,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并购Huntsman,交易金额达106亿美元。由于Hexion迫切期望并购Huntsman,因而其不但出价比其他竞争对手高出许多,而且在《合并协议》中承诺了许多严苛的条件,包括"No Financing Out"条款,也即并购方即使不能获得融资,也不得免于履行合同。
《合并协议》签订后,在双方申请并购交易相关监管批准的过程中,Huntsman披露的近几个季度的业绩表现令人失望,远未达到《合并协议》签署时的预测值。收到标的公司2008年第一个季度的业绩报告后,Hexion开始谋划如何退出交易。起初,Hexion考虑Huntsman是否遭受重大不利影响。之后,Hexion的关注点转向合并后的公司是否具有偿债能力,并聘请一家专业机构出具了一份关于合并后的公司无清偿能力意见(Insolvency Opinion)。2008年6月18日,Hexion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由于合并后的公司将缺乏偿债能力以及Huntsman遭受重大不利影响,致其无法获得融资,其将不会完成并购Huntsman的交易。随即,Hexion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在合并后的公司缺乏偿债能力的情况下其无义务完成并购Huntsman的交易,并且其对Huntsman的责任仅限于支付《合并协议》约定的分手费。同时,Hexion请求法院确认Huntsman遭受重大不利影响,因而,依照《合并协议》,Hexion免于承担完成并购Huntsman交易的义务。2008年7月2日,Huntsman向法院提起抗辩和反诉,请求法院判令Hexion履行《合并协议》。
法院在审理Hexion提出的关于Huntsman遭受重大不利影响因而免于履行《合并协议》的请求时,首先重申了In Re IBP一案确立的原则,即标的公司盈利的短期暂时性不利变化不足以被视为"重大不利影响",相反,不利变化只有从一个理性的并购方的长远角度来审视达到"重大"程度方可被认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标的公司在《合并协议》签署后至交割前这一段期间盈利严重下降的证据对判定"重大不利影响"毫不相干;标的公司在该期间盈利严重下降如果要被视为"重大不利影响",必须是其糟糕的业绩表现预期在将来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10]
其次,法院认为,使用每股盈利(Earnings Per Share)作为判断标的公司经营业绩变化的标准,在现金并购交易中是有问题的。每股盈利与公司的资本结构有关,反映公司的债务杠杆。而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独立于资本结构,能够更好地衡量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毫无疑问,Huntsman自协议签署日至2008年上半年结束的期间内经营业绩的确令人失望:2008年上半年Huntsman的EBITDA比2007年同期下降19.9%;2007年下半年的EBITDA比预测值低22%。但是,2007年第二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Huntsman的EBITDA比2007年同期降低仅仅6%。同时,法院指出,Huntsman的业绩未达到预测值,对判定"重大不利影响"没有关系,因为Huntsman在《合并协议》中已经明确排除其对业绩预测的任何保证。
最后,法院判定,鉴于Huntsman所面临的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原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急剧上涨及汇率变动引起的严峻宏观经济环境,Huntsman的业绩表现尚不足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法院进一步指出,并购方企图援用"重大不利影响"条款避免其交割义务,将面临非常沉重的举证责任,[11]而本案中,Hexion未达到这一举证责任要求。
六、Akorn v. Fresenius一案的判决意见
Akorn v. Fresenius一案的判决意见,近乎一半的内容是对事实的陈述,剩余部分几乎皆是关于"重大不利影响"的内容,涉及对《合并协议》中"重大不利影响"的定义、陈述和保证部分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交割条件部分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以及协议解除部分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梳理和分析,篇幅冗长。以下,笔者仅对案件事实和判决意见做简单摘要。
(一)
案件事实
并购方Fresenius和标的公司Akorn是两家制药企业,前者总部位于德国,后者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2017年4月24日,Fresenius与Akorn签订《合并协议》,以每股34美元的价格并购Akorn,交易金额达47.5亿美元。协议约定的交割最终日为2018年4月24日;如果届时反垄断审查是唯一没有满足的交割条件,则该日期自动延长至2018年7月24日。
《合并协议》签订后不久,Akorn的业绩出现断崖式下跌。2017年第二季度,Akorn的业绩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大幅下降,2017年7月和8月份,Akorn的业绩继续下滑。2017年9月份,Fresenius的管理层开始担心Akorn是否遭受"重大不利影响"。2017年10月,Fresenius收到一封匿名信,称Akorn的产品研发过程不符合监管要求。2017年11月,Fresenius收到一封更长的匿名信,披露了Akorn存在质量合规问题的更多细节。随后,Fresenius就该两封信所述问题启动调查。通过调查,Fresenius发现Akorn存在严重违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关于数据真实性要求(Data Integrity Requirement)的问题。在调查期间,Akorn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
2018年4月22日,即《合并协议》约定的交割最终日的两天之前,Fresenius通知Akorn解除《合并协议》。Fresenius声称,Akorn严重违反FDA对数据真实性的要求已导致Akorn在《合并协议》中关于监管合规的陈述和保证严重不实,该等严重不实已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同时,Akorn经营业绩的大幅下滑本身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根据《合并协议》交割条件部分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Fresenius有权拒绝完成交割。Akorn随即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Fresenius对《合并协议》的解除无效,并要求法院判令Fresenius履行交割义务。Fresenius提出抗辩和反诉,主张其已经有效地解除《合并协议》,而且按照《合并协议》,其无义务完成交割。
(二)
判决理由
在Akorn v. Fresenius一案判决意见的法律分析部分,法院一开始即指出,本案取决于《合并协议》约定的下述三个交割条件是否满足:(1)概括性"重大不利影响"条件:自《合并协议》日期起,Akorn未遭受重大不利影响;(2)"下拉"条件:Akorn的陈述和保证于交割日是真实和准确的,除非任何不真实和不准确不会单独或者共同一起合理预期产生"重大不利影响";(3)遵守承诺条件(Covenant Compliance Condition):Akorn必须已经在所有实质方面遵守或履行《合并协议》要求其在交割日之前必须遵守或履行的义务。[12]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交割条件未获满足,Fresenius都有权拒绝完成交割。
正如Akorn v. Fresenius一案判决意见所言明,长久以来,对"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争论,主要集中于概括性"重大不利影响"条款。是故,下文仅对Akorn v. Fresenius一案关于概括性"重大不利影响"条款的判决理由予以简述,而不论及其他。
法院指出,在任何并购交易中,签约至交割期间标的公司业务的严重恶化可能会威胁交易的基础,并购协议通过复杂和经反复磋商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来应对这一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典型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基本上没有对何谓"重大"进行明确定义。因此,对何为"重大不利影响"以及是否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问题,只能在交易一方援用"重大不利影响"条款并诉诸法院时,由审理法院来回答。
首先,法院认为,分析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第一步是确定标的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在程度上是否构成"重大"(Material)。法院承袭了In Re IBP一案和Hexion v. Huntsman一案的观点,强调"重大不利影响"必须是对标的公司在"商业上合理的期限"内的盈利能力具有重大实质影响,而该"商业上合理的期限"应当用"年"而非"月"来衡量。在法院看来,Hexion v. Huntsman一案已经明确表明,衡量标的公司业绩下降的程度,应当与其上一年同期的业绩进行比较,以消除季节性影响。法院引用学者的论文,认为利润下降40%以上或连续两个季度盈利下降50%可以判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但法院申明,这并不排除并购方能够举证证明低于上述幅度的变化亦可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排除并购方不能举证证明高于上述幅度的变化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法院的意见,本案中Fresenius已经举证证明概括性"重大不利影响"的发生。Fresenius的专家证人令人信服的证明Akorn的经营业绩自《合并协议》签署后发生严重下降,并且导致该等业绩下降的基础成因持续时间足够长。Akorn在2017年第二季度的业务收入(Revenue)、经营利润(Operating Income)和每股盈利(EPS)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9%、84%和96%;2017年第三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9%、89%和105%;2017年第四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34%、292%和300%;2017年全年与上年相比分别下降25%、105%和113%;2018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7%、134%和170%。Akorn在2017年全年的EBITDA与上年相比下降86%,经调整的EBITDA下降51%。这些数据表明,Akorn的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出现剧烈下降,并且其经营利润和每股盈利从正值变成负值。
法院指出,从更长的期限来看,Akorn于2017年度的业绩表现严重偏离其历史发展趋势。在自2012年到2016年的五年期间内,Akorn的业务收入、EBITDA、EBIT(息税前利润)和每股盈利每年持续增长。而在2017年,Akorn的这几个业务指标均发生严重下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合并协议》签署之前的2017年第一季度,Akorn的经营业绩并未显示下降的趋势,但在《合并协议》签署后,Akorn的经营业绩立即发生断崖式下跌。
法院进一步指出,Akorn经营业绩的严重下降已经持续一年时间,没有减缓的趋势,并且,引起该等业绩下降的基础成因也持续足够长的时间。Akorn的业绩下降并非暂时性的因素所引起,而是由于市场上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致使产品销售价格出现意料之外的大幅下跌,以及Akorn失去了一份关键合同。同时,法院认为市场上的估值分析也为Akorn的价值严重缩水提供了佐证。《合并协议》签署前,JP摩根对Akorn的估值为每股32.13美元;但是,鉴于《合并协议》签署后Akorn糟糕的业绩表现,评估机构给Akorn的估值为每股5至12美元,差异巨大。
Akorn辩称,评估Akorn价值的下降,不应仅基于Akorn本身的业绩表现,而应基于实现合并后实体的协同价值。法院不同意Akorn的这个观点。法院指出,根据"重大不利影响"的定义,"重大不利影响"的客体被十分明晰地界定为"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实体作为一个整体的业务、经营业绩或财务状况",而非合并后的实体。Akorn进一步辩称,只要Fresenius能够从该并购交易中获利,就不应认定发生"重大不利影响"。法院也不同意Akorn的这个观点。法院认为,"重大不利影响"的定义并无任何关于并购方从该并购交易中是否获利的内容;"重大不利影响"的定义只关注标的公司的价值。
其次,法院指出,只有在认定标的公司已经发生"重大不利影响"定义之"基本含义"部分所描述的"重大不利影响"之后,法院才会考虑是否适用"重大不利影响"定义所列的"除外情形"。Akorn的代理律师将Akorn糟糕的业绩表现归因于2013年以来影响整个制药行业的不利形势。法院认为,尽管根据"重大不利影响"的"除外情形",由于任何普遍影响标的公司所在行业的因素所引起的重大不利影响,不应认定为"重大不利影响"。但是,根据"重大不利影响"定义所约定的"除外情形之例外",如果普遍影响标的公司所在行业的任何因素,对标的公司的不利影响程度超过对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的不利影响程度,则该等超出的不利影响可以被认定为"重大不利影响"。
法院注意到,Akorn的业绩下降主要是由于市场上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致使产品销售价格出现意料之外的大幅下跌,以及Akorn失去了一份关键合同。这些因素并非影响整个行业的因素,而是Akorn自身经营出现的问题所致。同时,Fresenius的专家证人比较了Akorn与JP摩根在出具公允意见(Fairness Opinion)时所选择的部分业内同行于2017年第二、第三、第四季度和2017年度全年以及2018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发现Akorn在业务收入、EBITDA、EBIT和每股盈利方面,大大低于这些业内同行的平均值。因此,法院认为,即使Akorn如其所称遭受了行业不利形势的影响,但是行业不利形势对Akorn的不利影响程度严重超过对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的不利影响程度,因而,Akorn主张适用"重大不利影响"之"除外情形"的抗辩不能成立。
综上,法院总结道,Fresenius已经完成其举证责任证明Akorn的业绩下降从一个理性的并购者的长期视野来看已经构成"重大",并且,Fresenius也举证证明Akorn的业绩下降系由于Akorn自身的问题所引起,而非影响整个行业的不利因素所致。是故,Akorn遭受了概括性"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合并协议》所约定的交割条件未获满足,Fresenius有权不进行交割,并可行使其解除权解除《合并协议》。
七、结语
无可置疑地,Akorn v. Fresenius一案开创了一个先例,其对并购交易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重大不利影响"条款原本是为了应对不确定的情势而创设的一种交易保护机制,然而,如果并购交易各方动辄援用"重大不利影响"条款主张退出交易,势必将制造更大的交易不确定性。在这个日益不确定的时代,Akorn v. Fresenius一案将很有可能使并购交易变得愈益不确定。
注:
[1]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在我国《合同法》下,不可抗力条款的法理基础是"目的落空",而非"履约不能"。
[2]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根据该条,"情势变更原则"的法理基础既包括了"履约不能",也包括"目的落空"。
[3]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该条适用于一方违约导致的合同目的落空,即所谓的"根本违约",尚不属于普通法所说的"目的落空"。
[4] 参见Akorn v. Fresenius,第141页("It is not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sophisticated parties to merger agreements, who expend considerable resources drafting and negotiating MAC clauses, intend them to do nothing more than restate the default rule)。
[5] 美国法院做出的判决具有两类判例效力:有约束力的判例(Binding stare decisis effect)和有说服力的判例(Persuasive stare decisis effect)。对此,笔者不再赘述。
[6] In re IBP, Inc. S’holders Litig., 789 A.2d 14 (Del. Ch. 2001)。
[7] Hexion Specialty Chems., Inc. v. Huntsman Corp., 965 A.2d 715, 739 (Del. Ch. 2008)。
[8] 参见In re IBP(To such an acquiror, the important thing is whether the company has suffered a Material Adverse Effect in its business or results of operations that is consequential to the company's earnings power over a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period, which one would think would be measured in years rather than months)。
[9] 参见In re IBP(As a result, even where a Material Adverse Effect condition is as broadly written as the one in the Merger Agreement, that provision is best read as a backstop protecting the acquiror from the occurrence of unknown events that substantially threaten the overall earnings potential of the target in a durationally-significant manner. A short-term hiccup in earnings should not suffice; rather the Material Adverse Effect should be material when viewed from the longer-term perspective of a reasonable acquiror)。
[10] 参见Hexion v. Huntsman(This, of course, is not to say that evidence of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earnings by the target corpo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after signing but prior to the time appointed for closing is irrelevant. Rather, it means that for such a decline to constitute a material adverse effect, poor earnings results must be expected to persist significantly into the future)。
[11] 参见Hexion v. Huntsman(A buyer faces a heavy burden when it attempts to invoke a material adverse effect clause in order to avoid its obligation to close)。
[12] 参见Akorn v. Fresenius,第112-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