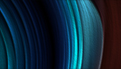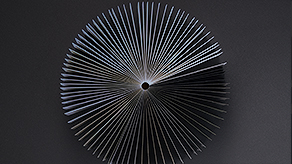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对不可抗力条款的重新审视
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对不可抗力条款的重新审视
合同制度是国际贸易的私法基础,合同的价值在于固定合同各方的交易预期和风险分配。日益频繁、扩张和激烈的经济制裁、进出口管制和其他贸易限制政策以及关税战等,使得国际公法所构建的国际贸易秩序遭受破坏、国际贸易环境日趋恶化、国际贸易风险急剧增加。虽然国际贸易会因此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但国际贸易不会因此而消亡。只要国际贸易一息尚存,任何一项具体的交易依然需要缔结合同并受其规制。作为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事主体,对国际贸易环境的激变也许无能为力,但面临每一项具体的交易,依然需要冷静和理性地从合同制度中寻求应对之策。
如同在疫情时期,人们纷纷求助于“不可抗力”制度以达到缓释交易风险之目的一样,在当下国际贸易环境风云骤变的新形势下,通过在国际贸易合同中设置适当的不可抗力条款来分配和控制风险,亦成为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事主体的一项自然选择。然而,时移势易,如何使“古老”的不可抗力制度适应当下“百年未遇之变局”,并达到分配和控制风险之目的,需要根据合同制度对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复杂的现实问题进行专业的分析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现实可行和有价值的建议。本文旨在对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定和不可抗力条款在当前环境下的适用进行审视,根据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对国际贸易合同中不可抗力条款的内容设计进行新的思考,并基于现实的考虑提出不可抗力条款的补充和替代条款。
一、不可抗力的法律规定
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不可抗力系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如果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则可依据默认规则(Default Rules)或缺失填补规则(Gap Filler)主张适用法律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中国亦是如此,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不可抗力系不履行合同的法定免责事由,也即在不可抗力致合同一方迟延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时,免除其迟延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责任。同时,在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下,不可抗力构成法定的合同解除事由。然而,法律规定的构成不可抗力的认定门槛较高,如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也就是说,一项事件,需同时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构成要件方可被认定为构成不可抗力。然而,证明前述三项构成要件同时满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笔者对近年来我国法院做出的涉及不可抗力案件判决的公开检索,合同一方主张经济制裁和贸易管制等情形构成不可抗力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主要原因是该等情形无法满足“不能预见”或“不能克服”的要件。例如,在昆明加加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与云南福瑞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行纪合同纠纷一案中[1],原告作为委托人与被告作为代理人签订一份代理进口协议,由被告代理原告与俄罗斯卖方签订进口合同,进口玉米浆干粉。被告收到原告以人民币支付的货款后,以美元向俄罗斯卖方支付货款,但货款支付后被美国花旗银行冻结。俄罗斯的卖方由于未收到货款,拒绝交付货物。于是,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进口合同没有全部履行的直接原因是被告支付的货款被外国政府冻结,这是被告不可抗拒的因素,但并非不可预见、不可避免,故不属于不可抗力。又如,在德阳万达重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四川科友电器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2],原告与被告签订一份分包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供应伊朗35万吨钢铁厂厂区供电系统成套设备。被告未能履行合同,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货款。被告辩称由于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昆仑银行无法正常交易,属于不可抗力。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案涉合同中被告的主要义务为货款支付,即使被告之合同相对方因昆仑银行的原因无法向其支付货款,可能会影响被告在案涉合同项下的履行能力,但此并不属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不能构成案涉合同无法履行的不可抗力事由。此外,关税增加导致一方履行合同成本的增加,按照中国法律的规定,也很难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因为其尚未达到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程度,因而不属于“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在许多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不可抗力并非源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出自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中未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则当事人不能主张不可抗力,但可依据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或履行艰难(Impracticability)等普通法原则或法律规定寻求救济。按照目的落空原则(Frustration of Purpose),如果发生一项一方在合同签订时不能合理预见的意外事件,致使该一方的合同目的完全或几乎完全落空,并且该一方的合同目的系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所知悉,则该一方可免于履行合同。而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或履行不可行(Impracticability)是指在合同订立后发生一项意外事件,致使一方履行合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如新的法律的颁布使该一方履行该合同成为不合法(Illegality),或致使一方履行合同遭受超出其预期的极度不合理的困难或费用,在此情形下,该一方可免于履行合同。例如,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第2-615条规定,如果卖方由于发生一项意外事件(该意外事件的不发生系其签订合同的基础条件),或由于其善意遵守适用的国内或国外的政府部门的规定或命令(不论该等规定或命令是否事后被证明无效),致使其履行合同实际上不可行,则其迟延交付或未交付不构成违约,但前提是不存在商业上合理可行的其他替代方式。在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于2023年9月就S*Energy, Inc. v. PDV, S.A. 一案作出的判决中[3],该案的法官认为,“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又称履行不可行(Impracticability),是纽约州法律规定的关于免于承担不履行合同义务之责任的一项积极抗辩(Impossibility, also known as impracticability, is an affirmative defense under New York Law against liability for non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然而,如果合同的履行不能或履行不可行系由于一方的财务困难、经济艰难甚至缺乏清偿能力,则履行合同的义务不得免除;并且,援引该抗辩的一方必须证明其已经采取其能力范围内的所有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履行其合同义务。该案中,被告系一家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其以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0月颁布的一项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禁止美国人与被告进行交易为由,主张依据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免于履行案涉票据(Note)项下的付款义务,但法官驳回了其主张,理由是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从未尝试通过不同的银行或以另一种货币履行付款义务,也未调查通过不同的银行或以另一种货币履行付款义务是否确实不可行,因而,被告未能证明其付款义务在客观上确实不可能。由此可见,合同一方依据普通法系国家关于目的落空(Frustration of Purpose)、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或履行不可行(Impracticability)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定寻求免责,也面临很高的门槛。
作为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第79条系关于“免责”(Exemption)的规定,通常被解释为包含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Change of Circumstance)导致履行极度艰难(Hardship)的情形[4]。但CISG第79条未使用“不可抗力”这一术语,而是使用了含义更为模糊的“障碍”(Impediment)一词。构成CISG第79条所谓的“障碍”,普遍的观点是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无法控制、无法预见、无法克服。该等条件与我国《民法典》关于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基本相同。然而,CISG第79条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应用障碍,其中一个原因是CISG第79条仅规定免除受“障碍”影响的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损失赔偿责任,而未免除其具体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的义务。此外,根据CISG咨询理事会关于第79条之意见的评注,截止该意见发布之时即2007年10月,也即CISG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后的近二十年之后,买方和卖方在诉讼和仲裁中援引CISG第79条获得成功的情况极为有限[5]。
二、合同中不可抗力条款的效力
如上文所述,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对不可抗力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未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则可以主张直接适用法律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不可抗力条款,该等不可抗力条款的效力究竟如何,这似乎并不是一个简单易答的问题。我国《民法典》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就不可抗力另行做出不同约定,学界对《民法典》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究竟是属于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亦存在较大争议。但从司法判例来看,笔者总结法院的多数态度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很大程度上认可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
总体而言,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可以归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不可抗力条款约定的构成不可抗力的条件、及不可抗力的范围与法律的规定基本一致,此类不可抗力条款自然会得到法院的认可;第二类不可抗力条款约定的构成不可抗力的条件、及不可抗力的范围宽于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范围,就此类约定,法院通常会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认为超出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范围的情形,在性质上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而属于当事人通过合意达成的附条件的免责条款,法院以审查一般合同条款的标准审查和适用此类约定:若此类约定若具备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不属于法定无效的格式条款,也不属于法定无效的免责条款,则约定有效,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第三类不可抗力条款对构成不可抗力的条件、及不可抗力的范围进行限缩,将某些依照法律规定本应属于不可抗力的事件排除在外,就此类排除,法院不认可其效力,依然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进行判定;第四类不可抗力条款完全将不可抗力排除于免责事由之外,即约定在任何情形下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均不得免责,此类约定因与法律规定不符,自然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6]
在2023年11月30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就JSC Power Machines v. Vietnam Oil and Gas Group and Petrovietnam Technical Service Corporation一案做出的仲裁裁决中[7],申请人声称美国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构成不可抗力,主张其有权根据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解除合同;仲裁庭经审理认为,美国对申请人实施的经济制裁并不构成不可抗力。该案中,申请人系一家俄罗斯公司,被申请人系一家越南公司。2014年申请人作为总承包商与被申请人作为业主签订了一份关于热电站的EPC合同。2018年,美国财政部以申请人与Siemens AG在俄罗斯设立的合资公司向俄罗斯批准建设的克什米尔热电站供应发电机组为由,将申请人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SDN清单”)。此后,申请人的分包商纷纷终止与申请人的合作,申请人无法继续履行EPC合同,遂于2019年1月以美国制裁构成不可抗力为由,依据EPC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书面通知被申请人解除EPC合同,并根据EPC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请求仲裁庭确认其已经有效地解除了EPC合同,同时请求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EPC合同项下欠付的款项和利息等。EPC合同适用的法律为越南法律,越南法律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与我国法律的规定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该案的仲裁庭并未纠结于是适用越南法律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还是适用EPC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作为判断不可抗力的依据,而是认为越南法律所规定的关于认定构成不可抗力的标准相较于EPC合同不可抗力条款的约定更为严苛,即使适用EPC合同的不可抗力条款,美国对申请人实施的经济制裁并不构成不可抗力,理由如下:首先,虽然申请人不能控制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但是能够控制引发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的事由的发生;申请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合资公司向克什米尔供应发电机组会触发美国的制裁,但其作为合资公司的一方并未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因而美国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并非其不能控制的事件;其次,美国对申请人实施经济制裁后,申请人并未采取积极合理的措施申请美国财政部将其移除SND清单,并且,申请人仍然参与合资公司并继续与被美国制裁的其他对象进行交易,因而,申请人并未采取合理的措施避免或克服案涉美国制裁。
相较于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的合同法更倾向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除有限的情形外,允许当事人对合同条款进行自由约定。因而,如果当事人期望通过援引不可抗力来分配合同履行的风险,应当在合同中约定明确、清晰的不可抗力条款。然而,法院在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时并不会一味地遵从当事人的约定,而会依据普通法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或履行不可行(Impracticability)原则、诚信原则(Good Faith)或合同解释规则,对当事人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进行限制。例如,在美国德州上诉法院于2018年就TEC Olmos, LLC v. ConocoPhillips Co.一案作出的判决中[8],法院就对当事人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进行了限制适用。该案中,当事人签订的一份石油钻井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约定:如果由于火灾、洪水、风暴、自然灾害、政府部门的行为、劳动争议、战争或任何其他未列举但系受影响的一方不能控制的原因,受影响的一方可中止合同的履行[9]。原告由于油价下跌失去履行合同所需的融资支持,遂依据上述不可抗力条款中的“兜底”(Catch-all)约定寻求免责。法院判决认为:首先,虽然该不可抗力条款本身未明确将“不能预见”(Unforeseeability)约定为不可抗力的一项构成要件,但参考履行不能(Impossibility)或履行不可行(Impracticability)原则,该条之约定应当隐含“不能预见”(Unforeseeability)这一基本要求,油价下跌显然不属于“不能预见”的事项;其次,油价下跌与该不可抗力条款所列举的事项不属于同类事项,依据“同类并列”(ejusdem generis)的解释规则,应当理解为不包含在该条款的“兜底”(Catch-all)约定的范围之中。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请求。此外,普通法系的法院在解释不可抗力条款时,将“不能控制”(Beyond Control)和“不能避免或克服”(cannot be avoided or overcome)视为不可抗力的必备条件,理由是如果不可抗力能够为受影响的一方所控制,或能够被避免或被克服,则不应当视为不可抗力,这也是“不可抗力”这一术语所应有之含义。[10]
英国最高法院于2024年5月就RTI Ltd v MUR Shipping BV 一案做出的判决[11],值得特别关注。该案的纠纷产生于船东和租船人于2016年签订的一份货物运输合同(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 “COA”),船东系一家荷兰公司,租船人系一家在泽西岛设立的公司,运输的货物为铝矾土,目的地为乌克兰。2018年,租船人的母公司被美国财政部列入SDN清单,于是船东向租船人发送不可抗力通知,声称由于美国对租船人的经济制裁,船东继续履行合同将导致违反美国的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并且,租船人由于该制裁将无法按照COA的约定以美元向船东支付运费,从而使船东无法履行装货和卸货义务。于是,船东根据COA中的不可抗力条款向租船人发送不可抗力通知,要求解除COA。租船人根据COA的仲裁条款将双方的争议提交仲裁,仲裁庭的裁决认定由于船东拒绝接受租船人提出的以欧元代替美元支付运费的请求,船东未能按照COA中不可抗力条款的要求,尽合理的努力(Reasonable Endeavors)克服美国对租船人实施经济制裁产生的影响,因而船东关于不可抗力的主张不能成立。此后,船东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确认船东的合理努力义务是否意味着其应接受租船人以欧元(非合同约定的支付货币)代替美元(合同约定的支付货币)支付运费。一审法院判决认为,除非合同有明确的约定,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没有义务接受另一方非合同约定的履行,以避免或克服不可抗力的影响。因而,船东拒绝接受欧元代替美元支付运费不能被认定为未尽合理努力克服不可抗力的影响,从而推翻了仲裁庭的裁决。此案上诉至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支持了仲裁庭的裁决。后该案上诉至英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上诉法院的判决,维持一审法院的观点,也即:不可抗力条款关于尽合理努力以克服或避免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之义务,并不要求援引不可抗力的一方必须接受另一方非合同约定的履行,该一方可以要求另一方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如果该等履行被不可抗力事件所阻止,则该一方可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免责。该案的判决结果与上述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就Siemens Energy, Inc. v. Petroleos De Venezuela, S.A.一案的判决结果截然相反。
根据CISG第6条之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减损CISG的任何规定或改变其效力。因此,如果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适用CISG,则他们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不同于CISG第79条之规定的内容,但此种约定的效力究竟如何,笔者尚未检索到相关的案例。但依笔者的判断,各国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据CISG对不可抗力条款效力及适用的判定标准不会与上文所述有太大的差异。
三、不可抗力条款的设计
由于各国法律,包括适用的国际公约,关于不可抗力之规定的差异,以及各国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待合同中约定的不可抗力条款的态度不同,因而,不可能有一个适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抗力条款;同时,也不是任何一个不可抗力条款都能获得法院或仲裁机构的认可,达到预期的目的。因而,不可抗力条款绝非是一个不动脑筋、可以随意复制粘贴的合同模板条款(Boilerplate Clauses)。不可抗力条款的内容设计需要考虑每一项交易及其环境和风险的特殊性,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范围力争能够涵盖将来可能发生的所有风险事件,尤其关注对当事人最不利和最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对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双方当事人的处理程序、事件导致后果的责任分配和费用分担、合同的解除等进行明确的约定,真正使不可抗力条款实现控制风险和分配风险的目的。同时,约定不可抗力条款时,还应考虑合同所适用的法律以及争议解决方式对不可抗力条款的影响。
笔者以为,在国际贸易合同中约定不可抗力条款时,国际商会2020不可抗力和履行艰难条款(ICC Force Majeure and Hardship Clauses 2020)非常值得参考(“ICC不可抗力条款”)。ICC不可抗力条款考虑了各国法律关于不可抗力之规定的差异,在之前版本的基础上,对不可抗力条款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优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将疫情、货币和贸易限制、禁运、制裁等明确列入不可抗力的列举事件。ICC不可抗力条款分为长版(Long Form)和短版(Short Form)。长版的ICC不可抗力条款包含九部分内容:(1)不可抗力的定义(Definition):该定义采纳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普遍接受的关于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即“不能控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或克服”,但通过增加“合理”(reasonable or reasonably)一词进行限定,降低了构成不可抗力的门槛;(2)第三方不能履行(Non-performance by third parties):该部分内容与CISG第79条第(2)款的规定保持一致;(3)推定的不可抗力事件(Presumed Force Majeure Events):该部分列举了七类不可抗力事件,并推定该等列举事件满足不可抗力定义部分关于“不能控制、不能预见”的要件,因而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无需再举证证明该两项要件的满足(但另一方可提出相反的证据推翻该推定),但仍需举证证明“不能避免或克服”这一要件的满足,方可被认定为构成不可抗力;(4)通知(Notification):要求受影响的一方毫不迟延地将不可抗力事件通知另一方;(5)不可抗力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Force Majeure):与CISG第79条的规定不同,ICC不可抗力条款对不可抗力的后果进行了明确约定:成功援引不可抗力的一方免于履行合同义务,免于损害赔偿责任,并且免于其他违约救济(包括CISG第79条未予明确免除的具体履行),但前提是援引不可抗力的一方毫不迟延地通知另一方;如果通知迟延,则免责延迟至另一方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6)临时障碍(Temporary impediment):如果不可抗力的影响是暂时的,则前述不可抗力的后果仅适用于该不可抗力阻止受影响一方履行其合同义务的期间,障碍停止后,受影响的一方必须立即通知另一方;(7)减损义务(Duty to mitigate):受影响的一方有义务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以减低不可抗力的影响;(8)合同终止(Contract termination):如果不可抗力的持续影响实际上剥夺了合同双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即构成根本违约,则任何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如果不可抗力持续超过120天,任何一方可解除合同;(9)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合同解除后,任何一方在合同解除之前因另一方的合同履行而获得的利益,应以等值金额的货币返还对方。
ICC不可抗力条款基本上依据CISG而设计,因此国际贸易合同参考ICC不可抗力条款时,应根据合同适用的法律进行必要的调整。例如,如果适用的法律是中国法律,笔者建议在合同解除部分明确约定,当不可抗力持续超过一定期限时,双方确认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以满足《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要求,免去关于合同目的落空的举证责任。其次,在对不可抗力事件进行列举时,笔者建议根据具体交易的情况,将基于目前的形势及未来的趋势可能考虑到的风险进行明确列举,以免除或减轻就该等事件主张不可抗力时的举证责任。此外,不可抗力条款的内容,应尽可能清晰、具体、不产生歧义,不给法院和仲裁机构太多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空间。例如,如果双方期望将“关税暴涨”作为不可抗力事件进行列举,建议明确关税上涨的比例,如“关税一次性或累积上涨超过30%”等(以笔者的意见,关税上涨不超过30%很难被认定为不可抗力)。又如,为避免上述RTI Ltd v MUR Shipping BV一案的后果,不可抗力条款应明确约定,承担付款义务的一方在发生经济制裁或货币管制等情形时,有义务采用合同约定的货币以外的任何其他货币或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履行付款义务。最后,不可抗力条款应对不可抗力事件给一方或双方造成的损失和费用如何进行分配和分担进行明确的约定,以免产生不必要的争议。
四、不可抗力的补充或替代条款
如上所述,鉴于各国法律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不同,各国法院和仲裁机构对不可抗力条款的态度差异,以及认可不可抗力的门槛极高,无论如何精心设计的不可抗力条款,都存在不被法院或仲裁机构全部或部分认可的风险。因此,为弥补该等风险,笔者建议在合同中通过设置单独的条款,对某些重大不利的风险事项进行专门的约定,以增加合同的确定性。
制裁和出口管制条款(Sanction Clause/Export Regulation Clause):目前许多国际贸易合同中都设置了制裁和出口管制条款,对发生经济制裁或出口管制时合同履行的安排、双方责任的免除或分配、合同的解除及损失的分担等进行明确的约定。该等约定从条款结构上,可以单纯地设置为一项责任排除条款;或可以设置为一项条件条款,对条件以及条件满足后的后果进行约定;也可以设计为一项义务性条款,包括陈述和保证、承诺、损害赔偿及合同解除等内容。例如,国际商会(ICC)关于使用制裁条款指南(2014)的补充文件(Addendum to the ICC Guidance Paper on the use of Sanctions Clause (2014))(2020年5月执行)推出的跟单信用证和保函中使用的制裁条款(Sanction Clause)的样本条款(Sample Clause)[12],就是一项责任排除条款(尽管国际商会并不鼓励在跟单信用证和保函等贸易融资文件中使用制裁条款,但国际商会建议,如果银行决定使用制裁条款,应根据国际商会的样本条款制定清晰、明确的制裁条款)。又如,FOSFA(Federation of Oils, Seeds and Fats Association)的标准合同中,在不可抗力条款之后设置了一项“禁止”(Prohibition)条款,约定在合同交付期限内,如果由于法律对出口的禁止或限制妨碍了货物的交付,则交付期限应延长至该等禁止或限制事件消除后21天;如果该等禁止或限制持续30天,合同可以全部或部分解除。该条款即是一项义务性条款。
法律变动条款(Change in Law Clause):鉴于各国涉及国际贸易的法律包括关于所谓“强迫劳动”、环保、碳排放、关税等方面的法律变动越来越频繁,直接或间接影响合同的履行,增加合同履行的风险和成本。因此,国际贸易合同中可以(期限较长的国际贸易合同非常有必要)设置单独的法律变动条款,对合同签订后所适用的法律变化导致合同不能履行、迟延履行或履行成本的增加等事项进行明确约定,以对法律变动所产生的风险在合同双方之间进行分配。例如FDIC生产设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件(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Plant and Design-Build)中就约定了“因法律改变的调整”(Adjustments for Changes of Legislation),对因基准日后法律变动引起的工程延误和费用增减,承包商可以要求延期和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
关税风险分配条款(Tariff Risk Allocation Clause):在关税剧烈变动的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合同中非常有必要设置单独的关税风险分配条款,约定双方对合同履行期间增加或减少的关税(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等)进行分担和分享。笔者曾看到过一个非常有启发的案例,国际贸易合同中包含一项专门的关税条款,约定根据关税的增加幅度调整双方对增加的关税的分担比例:关税增幅≤10%,买方负担100%,卖方负担0%;关税增幅10-25%,买方负担70%,卖方负担30%;关税增幅>25%,买方负担50%,卖方负担50%。
价格调整条款(Price Adjustment Clause):对于因汇率变动、通货膨胀等因素引起的成本和价格变化的风险,国际贸易合同中可以约定专门的价格调整条款,通过专门的计算方法,对合同价格进行调整,从而对该等因素引起的风险进行分配。
五、结语
在新的极为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下,任何情绪化的宣泄均无济于事。危机中总有机会,困境中总有出路。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企业,面对新的风险应当冷静分析,摒弃急功近利的惯性思维,寻求扎实的专业意见,探索法律上可行的应对之策。
[注]
[1]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2018)云0112民初10128号。
[2]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6民终43号。
[3] S* Energy, Inc. v. PDV,S.A. (2d Cir. 2023).
[4] CISG Advisory Council Opinion No.7: Exemption of Liability for Damages under Article 79 of the CISG (Adopted by CISG-AC on 12 October 2007).
[5] 同上。
[6] 不可抗力条款及其解释,崔建远,《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7] JSC Power Machines v. Vietnam Oil and Gas Group and Petrovietnam Technical Service Corporation, SIAC Case No. ARB274/19/AB.
[8] See 555 s.w.3d 176, 181–86 (Tex. app. 2018).
[9] “The two parties had entered into an oil drilling contract that allowed for suspension of contractual performance ‘by reason of fre, food, storm, act of god, governmental authority, labor disputes, war or any other cause not enumerated herein but which is beyond the reasonable control of the Party whose performance is affected.’”,Eliminating the Common Law Limitations of Force Majeure Clauses, Ben Luo, 538 Cornell Law Review [Vol. 109:537].
[10] Eliminating the Common Law Limitations of Force Majeure Clauses, Ben Luo, 549 Cornell Law Review [Vol. 109:537]
[11] RTI Ltd v MUR Shipping BV, [2024] UKSC 18.
[12] ICC Sample Sanction Clause: [Notwithstanding anything to the contrary in the applicable ICC Rules or in this undertaking,] we disclaim liability for delay, non-return of documents, non-payment, or other action or inaction compelled by restrictive measures, counter measures or sanctions laws or regulations mandatorily applicable to us or to [our correspondent banks in] the relevant transaction.